爱的旅程,终点是你。 徐静蕾 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 0
徐静蕾 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 0
 徐静蕾 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 0
徐静蕾 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 0 烟瘾重的人常常会忘记带烟,就好像自认为游泳不错的人常会淹死。 安妮宝贝 《八月未央》 0
安妮宝贝 《八月未央》 0
 安妮宝贝 《八月未央》 0
安妮宝贝 《八月未央》 0你喜欢什么?
潜水。
我也是,你在那个论坛?
我在海里。
 吴昱翰 《李茶的姑妈》 1
吴昱翰 《李茶的姑妈》 1
潜水。
我也是,你在那个论坛?
我在海里。
 吴昱翰 《李茶的姑妈》 1
吴昱翰 《李茶的姑妈》 1炭也不能总是燃烧/日子平淡就好/有一种成功或许更重要/比如总不见老//何必翻云覆雨/何必勾心斗角/活得累 怎么可能活得美妙//蚕儿做茧 鸟儿做巢/人生贵在心儿能够逍遥//淡点名 淡点利/深了笑容 浅了烦恼 汪国真 《佚名》 1
汪国真 《佚名》 1
 汪国真 《佚名》 1
汪国真 《佚名》 1怨恨是贫穷最可贵的花朵。 卡森·麦卡勒斯 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 0
卡森·麦卡勒斯 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 0
 卡森·麦卡勒斯 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 0
卡森·麦卡勒斯 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 0熊的视力不好,俗称熊瞎子,都是白天外出觅食,太阳落山前赶回巢穴,因为天一黑它们就什么也看不见,行走困难。特别是带崽的母熊,心里惦记着宝宝,绝不会拖到太阳快落山了还不回家的。棕熊实行走婚制婚姻形态,也就是说,公熊和母熊只在发情期聚在一起,其他时间都各自分开生活,母熊单独抚养子女。为了确保安全,母熊在外出觅食前,都要把熊崽喂饱,然后用树叶将宝贝团团裹起来。熊崽吃饱奶后,倒头大睡,约三到四个小时后才会醒来。母熊就利用这段空闲,抓紧时间寻找食物。一般情况下,母熊总是在熊崽醒来前赶回窝巢。 母熊的时间掐得很准,就好像脑子里有一个精确的时钟。这是因为一旦错过时间,不懂事的熊崽醒来后,会爬出窝去,或发出叫声,母熊不在身边的话,毫无自卫能力的小熊崽便会遭遇不测。 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 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在一般人眼里,虎是森林之王,但闯荡山林的猎人却不这么认为,猎人会说“头猪二熊三虎”,意思是猪比虎凶猛也比虎危险。 有经验的猎人都知道,打野猪有个讲究,必须从侧面瞄准射击,如果是山地,还一定要从坡上往坡下打。那是因为野猪素有“拼命三郎”的诨号,如果从正面射击,万一没打中要害一枪使它毙命的话,受了伤的野猪会不顾一切朝枪响的地方猛扑过来。要是野猪在坡上而猎人在坡下,野猪会勇往直前飙飞而下,猎人根本来不及躲避。 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 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
沈石溪 《最后一头战象》 0本质上他是名乞丐。他每天都在向那些宽宏大量的人乞讨他们的缺点,然后加以疯狂的羞辱。 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 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宏阳,在路上,我一直在思考:自由是什么。我对它的定义应该与书本无异,就是一个人不受限制与约束,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意志与活动。而我缺乏的就是这种支配自己的能力,或者说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能力。出狱使这个问题暴露无遗。 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 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
阿乙 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 0魔既然想变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,久而久之,就对种种变化本身感到厌倦了。如此一来,魔就想为什么一定要变化成那些凶恶的形象呢?于是索性就变成了人的形象。魔变成了人自己。魔与人变成一体。当初,在人神合力的追击下,魔差一点就无处可逃,就在这关键的时候,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,那就是人的内心,藏在那暖烘烘的地方,人就没有办法了,魔却随时随地可以拱出头来作弄人一下。这时的人,就以为自己在跟自己斗争。迄今为止,历史学家都对人跟自己斗争的结果与未来感到相当悲观。他们已经写的书,将要写的书,如果并未说出什么真相,至少持之以恒地传达出来这么一种悲观的态度。俗谚说,牲口跑得太远,就会失去天赐给自己的牧场;话头不能扯得太远,否则就回不到故事出发的地方。 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 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切请白帐王再有宽限 我还要三天时间 她想 自己经过这种事故 已经学会怎么做一个贤淑雍容的王妃了 但格萨尔却还没有学会做一个智慧如海、洞察一切的万民之王 她要为此惋惜三天 这三天里珠牡真是心痛欲裂 他把一枚红宝石摆在面前 心痛最甚时 那坚固的红宝石崩然开裂 成了碎片 她对侍女说 看吧 天都知道我痛悔之心 大王却不知道 等他回来时告诉他 我身子走了 心却破碎在岭地了 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 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
阿来 《格萨尔王》 0那她年轻的时候,除了读书,什么都不干? 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 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阿来 《蘑菇圈》 0他们知道,在那个时代,如果有人像斯炯一样先是有了给水桶加盖般的荒唐新奇的想法,继而又说出有诅咒意味的话,那她就成了一个邪恶的女巫。旧时代的人和新时代的人有一样其实相当一致,就是相信现实中的灾难是因为一些灾难性的话语所造成。土司时代,斯炯会被土司派遣来的喇嘛宣布邪祟附身,而从人间消失。 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 阿来 《蘑菇圈》 0
阿来 《蘑菇圈》 0鹿眼睛很大,水汪汪的半球体,像是树上将坠未坠的巨大露珠。阿巴从鹿眼里看得见一个被曲面扭曲得有些怪异的世界。天空,云彩,树,山坡和自己。鹿眨一下眼睛,这个世界就消失。鹿睁开眼睛,这个世界就出现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这么回应鸟鸣的时候,阿巴有想要落泪的感觉。 心头一热,就有泪水盈满了眼眶。他想此时泪珠里一定也映照出一个世界。天空,山野,还有他频频回望的幽深的峡谷。一滴泪水落下去,这个世界就消失。又一颗泪水溢出眼眶,这个世界又出现。他想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培训班上那个佛教喇嘛背诵的《金刚经》里的话:一切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云中村的男人老去的时候,会变成两种样子。一种,脸上的皱纹刀削斧劈一般,喝酒吃肉,越来越像个男人。这样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毁坏掉身上的某个器官,会经受死亡的痛苦。还有一种,像喇嘛这样,身子变得矮小,远看,脸上的皮肤紧致光洁,像是一把擦亮了的铜壶,近看,则是布满细密到不可胜数的皱纹,像是岁月的冰面被巨力震动,均匀地破碎到了看不出破碎的程度。这种破碎使得他们的面容带上了女性的柔美。这种破碎看上去像是一直在微笑。喇嘛变成了后一种人。他每天只喝一些泉水,吃很少一点粮食。那食量不超过一只画眉。每天,他都会坐在阳光下,像是能从阳光中直接吸收能量。这种人会无疾而终,某天坐在树下,再不起来,脸上的笑意固定住了,好像临终之前,看见了天堂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后来,他又从墙缝里翻出了一枚家族徽章。以前云中村人家家都有这样一枚徽章。云中村人都是普通农家,没有重要文书需要签署,他们的徽章用樱桃木雕成,用途也寻常。做好一只馍,就在馍的正中盖上纹样。就像在村委会,在一张纸上盖上公章。馍在铁鏊片上两面烙过,再埋进火塘里的热灰里慢慢烘熟。云中村没有人能说出为什么要在馍上盖家族徽章。一件事物,当人们都说不出个道理来,那就意味着它将要在生活中消失了。后来,云中村人也懒得再在馍上盖章,这些家家都有的木刻徽章就从云中村消失了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不要怪罪人,不要怪罪神。不要怪罪命。不要怪罪大地。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,久了也想动下腿,伸个脚。唉,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,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,大地稍稍动一下,我们就受不了了。大地没想害我们,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生命以鸟的方式存在,真好。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 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阿来 《云中记》 0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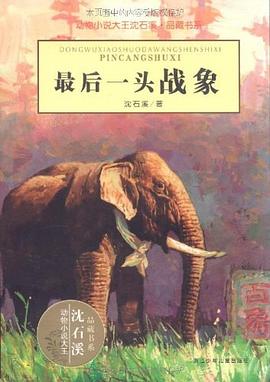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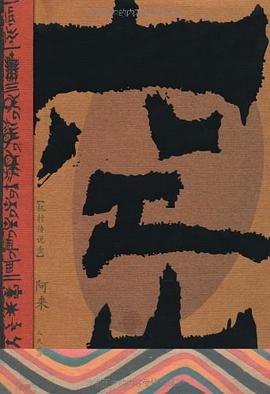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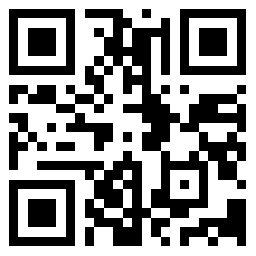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