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者的服装又叫装裹。所有的装裹,不论春夏秋冬都得用棉做成,禁忌用皮,据说是因为用皮之类的,死者下辈子会转世为牲口。所有的衣服也不钉纽扣,衣料也不能用缎子,因为“缎子”与“断子”谐音,“纽”与“扭”谐音,都是不利于后人的意思。
“一个黑暗森林中的猎手……突然看到……所有猎手都能认出的字标示出的森林中的一个位置……假设林中有一百万个猎手(在银河系上千亿颗恒星中存在的文明数量可能千百倍于此),可能有九十万个对这个标示不予理会;在剩下的十万个猎手中,可能有九万个对那个位置进行探测,证实其没有生物后也不予理会;那么在最后剩下的一万个猎手中,肯定有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:向那个位置开一枪试试,因为对技术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文明来说,攻击可能比探测省力,也比探测安全,如果那个位置真的什么都没有,自己也没什么损失。” 刘慈欣 《三体》0
刘慈欣 《三体》0
 刘慈欣 《三体》0
刘慈欣 《三体》0强力乃国家之本,德行乃为政之末。
 孙皓晖 《大秦帝国》1
孙皓晖 《大秦帝国》1
 孙皓晖 《大秦帝国》1
孙皓晖 《大秦帝国》1我现在每年买200本书,也就是每年在家里添一个双门书柜,书籍让我的居室和生活拥挤不堪。望着这些新旧不一的“朋友”,我终于发现,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单调的年代,也许没有一个年代的人、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——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们——像我们这样的五谷杂粮、精粗不弃,为了求得寸及的进步,我们愿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态,这是一个转型年代的特征,我们在思想上左冲右突,其慌乱和惊心宛若物质生活中的所有景象。
 吴晓波 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0
吴晓波 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0
 吴晓波 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0
吴晓波 《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0迄今为止,彻底摧毁过于残旧的文明成了群体最明确的任务,其实,并不是到了今天它才担此角色。历史告诉我们,一种文明,当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失去影响时,它也就被那些无意识的粗暴的群体最后解体了,用“野蛮”二字来形容群体是恰如其分的。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 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
古斯塔夫·勒庞 《乌合之众》1 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。 奥尔罕·帕慕克 《我的名字叫红》0
奥尔罕·帕慕克 《我的名字叫红》0
 奥尔罕·帕慕克 《我的名字叫红》0
奥尔罕·帕慕克 《我的名字叫红》0万千动物中,牛从来不与人为敌,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。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,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,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。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,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,牛的陪伴,牛的侍候。牛累了多少年,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,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。 余秋雨 《行者无疆》0
余秋雨 《行者无疆》0
 余秋雨 《行者无疆》0
余秋雨 《行者无疆》0中固海关是一栋崭新的大楼。九年前,它不在这里。我把行李放上传送带,排队给护照盖章。我的中亚之旅即将结束,我多少感到一丝澎湃的心潮:九年前,当我站在霍尔果斯口岸时,中亚还是一团迷雾。我渴望了解这里,填补我的世界图景——我就是带着这个上的旅程。如今,我从边境的另一侧回到了霍尔果斯,回到途最初开始的地方。我还记得自己当初的抱负和一路的辛劳。 与九年前相比,中亚不再陌生,但依旧神秘。我对中亚的热爱切如昔。经历过蒙古人侵、汗国争霸、苏俄重塑以及独立后的和复原,中亚又恢复了长久以来的模样一像一颗卫星,徘徊不同文明与势力之间,校正着自己的方位。我第一次去中亚时有这样的感觉。随着旅行的深入,这种感觉也愈加强烈。  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1
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1
 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1
刘子超 《失落的卫星》1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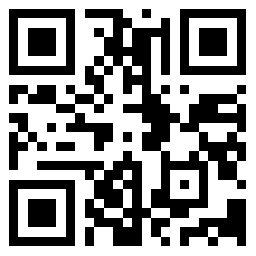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