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8月19日 星期一 不管怎样,我总以为书读得精细些并不为过,字里行间、每一个暗示都该看得真切些,显见的意思只是表面现象而已。但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:有时会曲解作者的情感。 最后一点是,希腊文化的独特魅力依旧,仍是那么撩人而难以捉摸。 希腊文学中的女主角与英国的非常相似,和艾米丽·勃朗特笔下的差不多。 厄勒克特拉属于视氏族(当然还有其父亲)高于一切的女性,和家族中的男孩子相比,她更重视伦理,觉得自己是与父亲而非母亲血肉相连。我很奇怪地注意到:尽管那些道德传统彻头彻尾地荒谬,他们却一点也不显得低贱卑微,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。
“当然没有错,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,但,元首,请看看我们的生活: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。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,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,个人不能工作就得死;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,法律只有两档:有罪和无罪,有罪处死,无罪释放。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单一和枯竭,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。我们没有文学没有艺术,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,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……元首,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?”——1379号监听员 刘慈欣 《三体》0
刘慈欣 《三体》0
 刘慈欣 《三体》0
刘慈欣 《三体》0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。语言是小说的本体,不是外部的,不只是形式、是技巧。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、他的思想(他的生活态度,不是理念)。必须由语言入手,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。语言具有文化性。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。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,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。包世成论王羲之字,看来参差不齐,但如老翁携带幼孙,顾盼有情,痛痒有关。好的语言正当如此。语言像树,枝干内部汁液流转,一枝摇,百枝摇。语言像水,是不能切割的。一篇作品的语言,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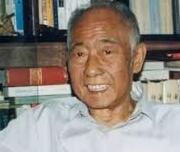 汪曾祺 《汪曾祺散文》1
汪曾祺 《汪曾祺散文》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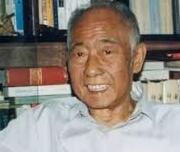 汪曾祺 《汪曾祺散文》1
汪曾祺 《汪曾祺散文》1我们的文化中一再强化血缘关系所带来的捆绑义务,却从不强调尊重人的个体完整性。也正是因为这些,很少有父母能跨越那道内心的障碍,把孩子当作一个完成而独立的人去看待,无论他们幼小还是成年。 杨时旸 《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》0
杨时旸 《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》0
 杨时旸 《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》0
杨时旸 《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》0地球村形成的速度不断加快,没有人能够阻挡。然而,只要保持对某种味道的迷恋和期待,那么这种味道,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生活信念,就一定会守护一个个不可复制的部落,一处处令人神往的秘境。 陈晓卿 《舌尖上的中国》1
陈晓卿 《舌尖上的中国》1
 陈晓卿 《舌尖上的中国》1
陈晓卿 《舌尖上的中国》1第一次走进台大文学院,就像走进中世纪巍峨的宫殿。高大的列柱,有着岁月抚摸的色泽,雕花的壁,总让人联想到神话。沿着石阶而上,踏着清脆的跫音,便有古老的浪漫自壁间回响出来。这里,永远有美的传说。 简媜 《水问》0
简媜 《水问》0
 简媜 《水问》0
简媜 《水问》0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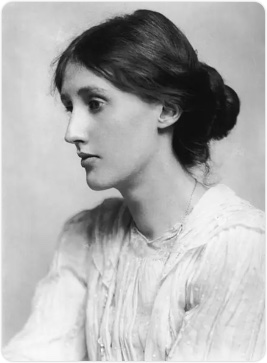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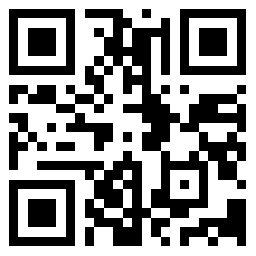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