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那时候明白了薛为什么想做外交官,她并非凭空生 出‘要成为一个外交官’的想法,而是从小就被植入了一 颗种子,种子到了时间,破壤生长。而我从小到大,连 ‘外交官’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几次,更不觉得它和自己有什么关联。就像我最早教过的那个男学生,毫不犹豫地说出‘当然是演奏家啦’,千条万条路,耳濡目染的只有这一条路,不选它选什么?那一瞬间,我觉得人大约只是个容器,早些年种下什么,后面收获什么,如果没有种下什么,或种子没有发芽,人就是空心的。乡村长大的人明白播种的时机有多么重要,一旦错过,接下来不管怎么补救,收成都不会好。 “其实薛和我之间悬殊的阶层差异并没有真正冲击到 我,我刚来北京就知道了,有钱的有权的人遍地都是,你以为和其他人身在一个世界,但其实并不在一个世界,差距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实,必须接受这种差距,才能心态平稳地活下去。只是薛并不真正明白,我吃了多少苦头,这些吃过的苦甚至凝结成一种特别的道德上的骄傲——我全靠自己,这份骄傲足以抵消我和薛之间的差异,至少道德上,我比她高贵。她肯定不认同这一点,但我心里就是这么认为的,所以我可以克服自卑,和她待在一起。但我无法忍受她在精神上表现出的坚定,她有梦想,而且愿意付出长足
当你觉得生活没意思,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时。说明,你已经许久没有做出改变了。长时间呆在舒适区,人难免慢慢丧失斗志。动起来,做出改变,出去看看世界,或者学习一个新技能,让自己始终在进步。你要相信,这个世界上,一定有另一个自己,在做着你不敢做的事,过着,你想过的生活。 佚名 《一禅小和尚》0
佚名 《一禅小和尚》0
 佚名 《一禅小和尚》0
佚名 《一禅小和尚》0我在做梦,我觉得时间走得没有尽头。没有“以前”,也没有“以后”,我也不期待任何新鲜事物,因为我既不能得到它,也不能失去它。夜永远不会结束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甚至时间也不会改变我看到的东西。我看着,我既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,也不会忘记我见到过的一切。 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0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0
 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0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《白天的房子,夜晚的房子》0我们在静谧的时间里,藏着秘密的爱情。 关东野客 《我有故事,你有酒吗?》0
关东野客 《我有故事,你有酒吗?》0
 关东野客 《我有故事,你有酒吗?》0
关东野客 《我有故事,你有酒吗?》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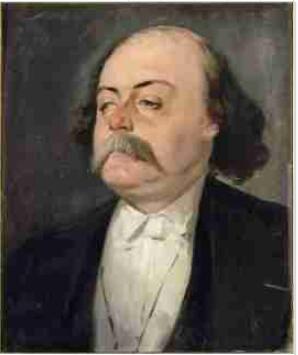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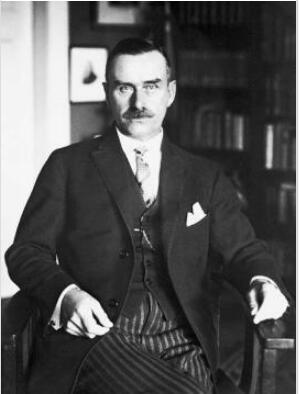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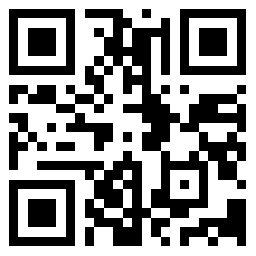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