乃至最可笑者,刘公岛降舰之役,当事者致书日军,求放还广丙一船,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,此次战役,与广东无涉云云。各国闻者,莫不笑之,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。若是乎,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。以一人而战一国,合肥合肥,虽败亦豪哉!
最富有的时候,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。吹毛求疵的人即便在天堂也能挑出瑕疵。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自得其乐的生活,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,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。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,无论衣服还是朋友。把旧的翻新,回到它们中去。万事万物没有变,是我们在变。 梭罗 《瓦尔登湖》0
梭罗 《瓦尔登湖》0
 梭罗 《瓦尔登湖》0
梭罗 《瓦尔登湖》0上天赐予我们每个人两样伟大的礼物:思想和时间。你可以运用这两件礼物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。每一美元钞票到了你的手中,你,且只有你,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。愚蠢的用掉它,你就选择了贫困,把钱用在负债项上,你就会成为中产阶级,投资于你的头脑,学习如何获取资产,富有将成为你的目标和你的未来。选择只能由你作出。每一天,面对一美元,你都在作出自己是成为一个富人、穷人还是中产阶级的抉择。 罗伯特·清崎 《富爸爸穷爸爸》0
罗伯特·清崎 《富爸爸穷爸爸》0
 罗伯特·清崎 《富爸爸穷爸爸》0
罗伯特·清崎 《富爸爸穷爸爸》0他(德·拉马尔子爵)生有一副漂亮的面孔,教女人见了钟情,教男人见了生厌。乌黑的卷发遮盖着光润的棕色的前额,两条匀称的长眉毛,象是特意修饰过的,使一双眼白微带蓝色的忧郁的眼睛显得幽深而温柔。浓长的睫毛使他的目光中添上一种热情的感染力,那会在客厅中使高傲的美妇人心乱,在街头上使头戴便帽手提篮子的贫家女儿顾盼。他的眼神里那种懒洋洋的惑人的魅力,教人相信他的思想深刻,使他所说的一言一语都增添了力量。他的浓厚的胡子,又光泽又细密,掩盖住了他那过方的腮骨。  莫泊桑 《一生》1
莫泊桑 《一生》1
 莫泊桑 《一生》1
莫泊桑 《一生》1当你不把你的思想指向公共福利的某个目标时,不要把你剩下的生命浪费在思考别人身上。因为,当你有这种思想时,你就丧失了做别的事情的机会。这个人在做什么,为什么做,他说了什么,想了什么,争论什么,注意所有这些事情将使我们忽略了观察我们自己的支配力量。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思想行进中抑制一切无目的和无价值的想法,以及大量好奇和恶意的情感。  马克·奥勒留 《沉思录》1
马克·奥勒留 《沉思录》1
 马克·奥勒留 《沉思录》1
马克·奥勒留 《沉思录》1任何试图将这些书视为机械意义上的“原始出处”的做法,都会在梅诺基奥独出心裁的解读面前溃不成军。如此一来,在文本之外,重要的其实是他解读这些书的方法,这是一层被他无意识地置于自身和印刷制品之间的滤网:这道滤网让某些字句得到了强调,而某些字句则遭掩盖混淆,还有某些字句被从其语境中割裂,含义被曲解;这道滤网作用于梅诺基奥的记忆,扭曲了真实的文本字句。而这道滤网,他的这种解读方法,一直把我们领回到一种截然不同于书面表达文化的文化——一种基于口头传统的文化。这并不意味着书本对于梅诺基奥而言不重要,或者只是装腔作势的道具。我们很快便将看到,他宣称,至少有一本书曾令自己感动至深,激励他思考那些语出惊人的新思想。事实上,正是印刷制品与口头文化的碰撞——而他便是这种碰撞的一个具体代表——让梅诺基奥想出了那些“他自己从脑袋里琢磨出来的看法”,那些他先是对着自己、然后当着乡里乡邻、最后面对宗教法庭的法官侃侃而谈的看法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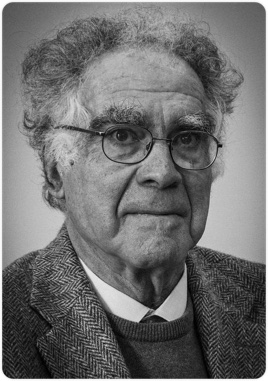 卡洛·金茨堡 《奶酪与蛆虫》0
卡洛·金茨堡 《奶酪与蛆虫》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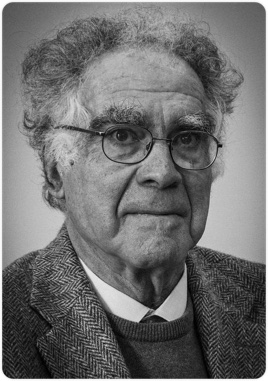 卡洛·金茨堡 《奶酪与蛆虫》0
卡洛·金茨堡 《奶酪与蛆虫》0但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他问我:“你父母同意了吗?”时年我已经二十九岁了,自认为已经过了做事情需要父母同意的年龄。对于这个问题,我感到十分困惑。也许在他的认知里,一个农村女子辞掉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大事;又或者,也许我们的社会,或者说我所工作的那座边境小城的文化体系里,一个单身的女子辞掉工作,是需要“管理者”,也就是父母同意的。 事实上,在长时间的成长和工作阶段,我经常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对待。我很惧怕集体的概念,我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集体生活的人,适应集体对我来讲真的太难了。读过加缪的《异乡人》之后,我对此尤其有更深的体会。集体,尤其是我见过的集体,是一种非常分裂的存在,它要求你与众不同以便“创新化”“多样化”,同时它要求你不能与众不同,必须“思想统一,服从安排,听从指挥”。 扎十一惹 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0
扎十一惹 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0
 扎十一惹 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0
扎十一惹 《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》0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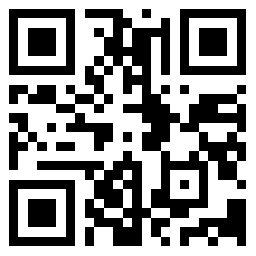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