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,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初具规模,它们投资多,营业的空间大,雇用的工人多,接纳的客人众,因此利润不菲。大茶馆的老板与地方政府的官员、军队和商界的头面人物,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,以得到保护。但那些小茶铺缺乏这些资源,资本少,规模小,利润低,无法再投资,故难以扩展,多数也仅处于糊口的水平。
企业创造了社会基因或者思想基因,这可以跨越企业的边界,影响到整个行业乃至社会,实现横向的传承。比如苹果,它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电脑或者手机单纯产品的范畴,影响也绝不仅仅限于苹果公司内部。甚至可以说,我们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苹果的烙印,这就是从0到1,企业创造的基因影响了社会文化和观念,乃至改变社会进程,这就是质变。 彼得·蒂尔 《从0到1》0
彼得·蒂尔 《从0到1》0
 彼得·蒂尔 《从0到1》0
彼得·蒂尔 《从0到1》0不是灭自家威风,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秀,实在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。数量少,二三十字以下,中文占绝对优势。有时候,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,比如“家”字,一片屋檐,一口肥猪,有屋睡有肉吃就是家。乱翻词谱,有时候,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完整的意象,比如“醉花阴”:丁香正好,春阳正艳,他枕在你的膝上,有没有借着酒意浓重树影朦胧说过让你面红的话?比如“点绛唇”:唇膏涂过,唇线描过,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,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眼睛?五言绝句,有时候,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,比如柳宗元的《江雪》,有天地人禽,有时间空间。 冯唐 《猪和蝴蝶》1
冯唐 《猪和蝴蝶》1
 冯唐 《猪和蝴蝶》1
冯唐 《猪和蝴蝶》1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,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,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。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。整个德国、法国、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,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,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,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,没有了去说、去写、去做的必要,那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,不知所云的东西。这种血腥的灾难,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。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。 雷马克 《西线无战事》0
雷马克 《西线无战事》0
 雷马克 《西线无战事》0
雷马克 《西线无战事》0现在的收藏大家马未都当初与我们一样,也是个码字的媒体人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他带上当时最流行的电镀折叠椅子,在北京西四等地信托商店或家具门市外面,等那些拿红木或更珍贵老家具来的主儿。上前商量着用电镀椅子换老家具,十有八九乐呵呵地同意。转眼二三十年过去,电镀椅子都锈了扔了,而换来的老家具则进了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馆,展览着,拿啥都不换。 白岩松 《白说》1
白岩松 《白说》1
 白岩松 《白说》1
白岩松 《白说》1









 句子抄安卓版
句子抄安卓版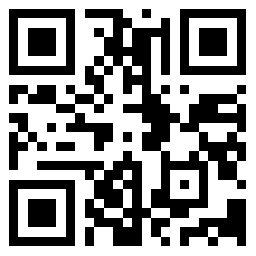 句子抄手机版
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
句子抄公众号